多动症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指发生于儿童时期,与同龄儿童相比,以明显注意集中困难、注意持续时间短暂、活动过度或冲动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综合征。多动症是在儿童中较为常见的一种障碍,其患病率一般报道为3%-5%,男女比例为4-9:1。
朴永馨身上有很多个第一
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特殊教育本科生和研究生、撰写了第一套特殊教育专业教材、创立我国高校第一个特教专业,填补了高等师范教育特殊教育的空白……
“我当时便称我的第一批学生是‘黄埔一期’,前五期学生是‘黄埔108将’,他们现在很多仍在特殊教育一线工作,有的已经成为教授、校长。”上午,朴永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专访,提起昔日的学生,他眼神里满是笑意。
“一五计划”时期,应国家对特教专业教师的需要,朴永馨和同学银春铭一起去苏联学习特殊教育。1961年,从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现为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毕业。回国后,朴永馨便投入特殊教育事业中,转眼就是半个多世纪。
回忆特教专业创立时的艰辛,谈政策变迁……87岁高龄的他思路清晰、逻辑缜密。
朴永馨见证了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变革。言谈中,他多次提到“平等”二字。朴永馨认为,特殊教育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热爱行业、尊重孩子、爱孩子。
如何评价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的发展?他用一句话形容:70年前,我们不在国际特殊教育事业的队伍里,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在这个队伍中和其他国家平行前进。
应国家需要留学苏联学习特殊教育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特教行业更是急需专业老师。“一五计划”时,你就被派到苏联留学,当时我国的特殊教育情况是怎样的?
朴永馨:1948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教育年鉴”中提到,当时我国特殊教育学校有42所,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是360人。旧中国,特殊教育并非大中小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是被归为社会教育,由教会、福利机构提供,属于慈善、救济性质,当时42所学校中,仅有一所国立、七所市立。
1951年,周恩来总理签署了《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将特殊教育变成新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如今,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288所,特殊教育专任教师将近7万人。以高等学校为例,专门招收残疾人的高校我国有23所,比如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学院等,这组数据在国际上都是比较高的。
新京报:看以往的报道,你在苏联求学时读了四个特教专业?
朴永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便提出要建立高等学校的特殊教育专业,我们被派到苏联留学就是要回来在大学中建设特教专业的。因为当时我国高校没有,国外大学中有这样的专业。
1956年,我和银春铭到了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特殊教育专业。苏联那时有针对聋哑、弱智、语言障碍、盲人的四个特殊教育专业,但我们只有两个人。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学一个特教专业,再选一个数学或语言的普通教育专业。但我想,要把人家特教的东西都学来,回国好用。
我们商量后,决定放弃普通教育专业,只学习特教专业。第一年跟着聋人特教专业学习一年级知识,升入二年级后我一边学聋人特教二年级知识,一边学习另一个特教专业的一年级知识,就这样到了第四年,我申请到列宁格勒出差,到那里学习盲人特教专业知识。如此,我们在国外学习了五年,把四个专业都学下来了。
回国后我本可以直接回到北师大建设特教专业,但我选择先到一线实践,再回到高校阵地。于是,我进入北京第二聋哑学校从事一线教学。

三十多年前,朴永馨在英国伦敦马克思墓前拍照留念,这里也是他久仰之地。 受访者供图
在特教专业成立之初也曾经历“招生难”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的一线特殊教育情况和现在有哪些不同?
朴永馨:现在招聘教师都标准化了,要求老师热爱工作、有学识等等,这些在教育部发布的文件中都有明确要求。此外,现在对教师的学历也有很高要求,好的学校会招研究生进入特教领域教学。
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连教学标准、大纲都没有。当时,缺老师就上街道办去问有没有来登记找工作的失业人口?合适就招进学校当老师。不指望教书,能看孩子就行。那时来当老师的有初中毕业生、家庭妇女。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把教学工作开展起来,之后一待就是近20年。其间,我也做了很多科普、调研的工作,也为一线学校做了点贡献。
直到“文革”后期,我提出想回到高校建特殊教育专业,因为国家一直有这个需要,北师大和教育部当时都很支持。1979年,我正式调到了北师大。其实,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对特殊教育教师待遇有倾斜,比普通教师的工资高15%。我调到北师大做老师后,反而降了两级工资(笑)。但我想,降工资也干,我可以在高校建设特殊教育的阵地。
新京报:不论从专业建设还是教材编著,你推动特教事业完成了多项从“0”到“1”的突破,其间遇到了哪些困难?
朴永馨:说实话,我也够大胆的。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是教育专业的主要科目。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特殊教育专业,招生时,我连教材都没有(苦笑)。
只有我一人设计专业课程。特殊教育学、特殊心理学、特殊教育史三门专业课,我不可能那么快把专业教材都编出来,只能先做提纲,亲自给学生上课。这三门专业课都是我一人上。
当时不仅没有教材,连办公室都没有,后来在系主任办公室给我放了一张桌子。就这样,我早晨去打扫卫生,系主任办公的时候,我就去图书馆工作,就这样逐渐编好了讲义和教材。
新京报:特殊教育专业刚成立时,是不是招生很困难?
朴永馨:对。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第一批招收了15名学生,但第一志愿填报这个专业的学生没有几个。看到专业名称叫“特殊教育”,有的学生问“是不是专门培养特级教师?”,还有的问“是不是培养特务间谍?”(笑)
当时也有学生愿意来,但家里不同意。我记得有个女生,她对象家里说,“你要搞这个,俩人就得吹”,人家就只能不干了呗。确实有艰难的过程。
当时,社会上对残疾人还有很深的误解。学生们招来之后,先做入学思想教育,普及相关理论,让他们了解特殊教育的内容,了解特殊教育教师的责任。
我让学生到福利院、特殊教育学校实地观察残疾人的生活和学习,也激发青年人的热情。我当时对他们说,你们想开垦处女地,特殊教育就是新兴学科。他们中很多人目前还在从事特殊教育。
希望建设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科理论
新京报:你见证了特殊教育事业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朴永馨:1988年,第一次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 “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重点”的方针,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教育体系明确了发展方向。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和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成了我国残疾儿童少年就学的三种主要形式。
我记得那次会议上,决议期间,我提出了两个意见,一是特殊教育不要只局限于小学教育,二是特殊教育不要只局限于盲、聋、弱智三类,要涵盖情绪障碍、语言障碍等情况,国家都采纳了。
199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中国残联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到“自有人类,就有残疾人。”这即说明社会发展中有人类就有残疾人,他们也是平等的人,也有权利有义务,这是我们特殊教育建设的理论基础。
我在几十年的特殊教育工作中领悟到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残疾人、怎么对待残疾人,这是特殊教育发展中很重要的问题。
从法律来看,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特别体现了对残障人士以及特殊教育的关心:“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在《宪法》中写进特殊教育为今后制定各种法律提供了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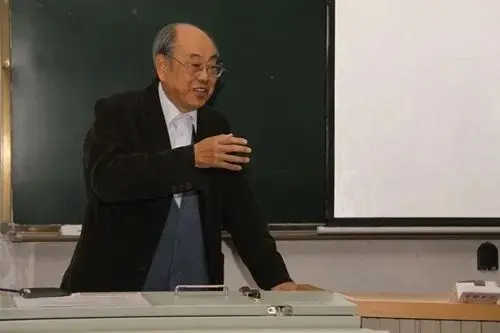
从党的文件来看,党的十七大将“关心特殊教育”首次写进报告中。之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又分别提出“支持特殊教育”“办好特殊教育”,让全国特教人备受鼓舞。特殊教育教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但在地位上有了提升,在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会议、教师评选中都能看见特教教师的身影。
新京报: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目前还有哪些壁垒有待突破?
朴永馨:对于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科的形成,我思考得较多。我去英国、以色列、美国参与特殊教育的会议、论坛,作为中国特殊教育领域的工作者,我已经能够比较平等地参与国际讨论。但是,目前我们很多时候还在讲外国理论,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被国际公认的、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科理论。
没有理论支撑,实践就是盲目的实践。我们拥有特殊教育专业的高等学校不仅要培养特教教师,更要进行理论研究,高等学校要承担起这一责任。
此外,在特殊教育专业方面,随着残疾人进入中学、高中,甚至大学,我们要重视特教中的学科教育。比如聋人的高中数学、地理、物理,聋校毕业的教师教不了,盲校教师仅会盲文也教不了这些学科。高等教育中的学科教育和特殊教育如何结合也需要研究。
我也一直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问题,鼓励学生到西南、新疆去。就像摆脱贫困一样,普及特殊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